前一頁
回目錄
波士頓賽爾提克籃球隊的球員羅素(Bill Ruesell)曾經如此描寫他們的球隊:“就像其他專業領域一樣,我們也是由一群專家組成的團体,我們的表現依靠個人的卓越以及團体的良好合作。我們都了解彼此有互相補足的必要,并努力設法使我們更有效地結合……。然而有趣的是,不在球場上時,按照社會的標准來看,我們多數是古怪的。絕不是那种能跟別人打成一片,或者刻意改變自己來迎合別人的人。”
羅素告訴我們,使他的球隊打起球來与眾不同的,不是友誼,而是一种團体關系。大伙儿在球場上的配合,使團体產生登峰造极的演出,那种高度的默契,難以用筆墨來形容,几乎像慢動作般的清楚,任何神奇的妙傳或投射都可以發揮到不可思議的境界。
潛在的團体智慧
羅素所屬的球隊(在十三個球季中得過十一次NBA總冠軍)呈現出一种我們稱之為“整体搭配”(alignment)的現象,即一群人良好地發揮了整体運作的功能。然而在多數的團体里,成員各自朝向交錯的目標努力。如果我們為這种團体畫一幅圖,看起來可能像是圖12—l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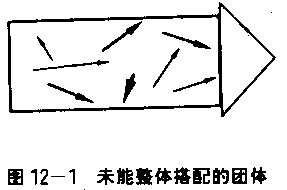 |
未能整体搭配的團体,許多個人的力量一定會被抵消浪費掉。個人可能格外努力,但是他們的努力未能有效地轉化為團体的力量。當一個團体更能整体搭配時,就會匯聚出共同的方向(圖12—2),調和個別力量,而使力量的抵消或浪費減至最小,發展出一种共鳴或綜效,就像凝聚成束的雷射光,而非分散的燈泡光;它具有目的一致性及共同愿景,并且了解如何彼此截長補短。
 |
這也不是指個人要為團体愿景而犧牲自己的利益;而是將共同愿景變成個人愿景的延伸。事實上,要不斷激發個人能量,以使團体力量提高的大前提,乃先要做到整体搭配。在團体中,如果個人的能量不斷增強,但是整体搭配的情形不良,只會造成混亂,而使團体的管理更加困難,如圖12—3所示。
“團体學習”是發展團体成員整体搭配与實現共同目標能力的過程。它是建立在發展“共同愿景”這一項修煉上。它也建立在“自我超越”上,因為有才能的團体是由有才能的個人所組成的。但是只有共同愿景和才能還不夠;世界上不乏由有才能之士所組成的團体,其成員雖然暫時共有一個愿景,卻無法共同學習。偉大的爵士樂團的先決條件,雖是擁有才能出眾的團員和一個共同愿景,但是真正重要的是這些音樂家知道怎樣一起演奏。
組織在今日尤其迫切需要團体學習;無論是管理團体,產品開發團体,或跨机能的工作小組。以殼牌石油企畫主任德格的話來說,團体就是彼此需要他人行動的一群人。而團体在組織中漸漸成為最關鍵的學習單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現在几乎所有重要決定都是直接或間接透過團体作成,而進一步付諸行動的。在某些層次上,個人學習与組織學習是無關的,即使個人始終都在學習,并不表示組織也在學習。但是如果是團体在學習,團体變成整個組織學習的一個小單位,他們可將所得到的共識化為行動;甚至可將這种團体學習技巧向別的團体推廣,進而建立起整個組織一起學習的風气与標准。
團体學習的三個面向
在組織內部,團体學習有三個面向需要顧及。首先,當需要深思复雜的議題時,團体必須學習如何革取出高于個人智力的團体智力。這說起來容易,但組織中常有一些強大的抵消和磨損力量,造成團体的智慧傾向小于個別成員的才智。這些力量有許多是可由團体成員加以控制的。
其次,需要既具有創新性而又協調一致的行動。在一流的球隊和爵士樂隊中,便常會發現這种既有自我發揮的空間,而又能協調一致的方式。在組織中,杰出團体也會發展出同樣的關系——一种“運作上的默契”;每一位團体成員都會非常留意其他成員,而且相信人人都會采取互相配合的方式行動。
第三,不可忽視團体成員在其他團体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影響。譬如高階管理團体大部分的行動,實際上是透過其他團体加以實現。因而,一個學習型的團体,可透過廣為教導團体學習的方法与技巧,不斷培養其他的學習型團体。
雖然團体學習涉及個人的學習能力,但基本上它是一項集体的修煉。因而,強調個人正在精進的團体學習修煉是沒有意義的。
團体學習的修煉必須精于運用“深度匯談”(dialogue)与“討論”,這是兩种不同的團体交談方式。深度匯談是自由和有創造性地探究复雜而重要的議題,先暫停個人的主觀思維,彼此用心聆听。討論則是提出不同的看法,并加以辯護。深度匯談与討論基本上是能互補的,但是多數團体缺乏區分及妥善運用這兩項交談技巧的能力。
團体學習也包括學習如何避開与上述這兩种有建設性的交談相反的巨大力量。其中首推阿吉瑞斯所稱的“習慣性防衛”——那些使我們及他人免受威脅与窘困的習慣性互動方式,它將阻礙我們的學習。譬如,在面對意見沖突時,團体成員往往不是折衷妥協,就是爭得你死我活。當解開學習性防衛的症結時,便可發掘出原先不曾注意的學習潛力。首先,我們必須運用第十章中所介紹的探詢与反思技巧,讓我們開始釋出這個能量,然后我們才得以專注于深度匯談与討論。
由于系統思考的中心信念是“我們的行動造成現況”,因此特別容易挑起自我防衛。為了避免別人指控是自己的策略造成這些問題,團体可能因而抗拒采用更有系統性的方式來察看問題。許多團体口頭上雖然擁護系統的觀點,但實際上卻從未付諸實行,從來不會用所有的心力來認真地檢驗自己的行動如何造成問題。系統思考需要一個真正成熟、能夠深入探究复雜与沖突議題的團体,才能實行。
最后,團体學習的修煉像任何的修煉一樣,都需要練習。這正是現代組織所缺乏的。試想一個從不排演的交響樂團,將如何演出?一個從不練習的球隊,將如何出賽?同樣的,任何團体的學習過程,都是透過不斷的練習与演出。目前我們還處于學習如何為管理團体創造類似練習机會的起步階段。第十八章介紹“微世界”時將提供几個例子作為說明。
盡管團体學習很重要,我們對它的了解卻非常貧乏,對它的許多理論和實踐方法,也都尚在試驗階段。我們必須要能更清楚地描述,當它發揮功能時的現象是如何?并且更明晰地區分,消极被動的“群体思考”,和真正有創造性的“群体智力”之不同。只有當我們能找回團体學習的有效方法,才能真正掌握建立杰出團体的要訣。這就是為什么精熟團体學習是建立學習型組織的一個關鍵步驟。
團体是學習的最佳單位
在《物理學及其他:相會与交談》(Physics and Bexond:Encounters and Conversations)這本引人注目的書中,海森堡(Werner Helsenberg,首先提出“測不准原理”[uncertalnty principle]的現代物理學者)認為:“科學根源于交談。在不同的人合作之下,可能孕育出极為重要的科學成果。”接下來海森堡回憶平生与鮑立(Pauli)、愛因斯坦(Einstein)、波耳(Bohr),以及其他在這個世紀前半葉改造傳統物理學等偉大人物的交談。這些海森堡認為對他的思考有不可磨滅影響的交談,在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許多使這些人后來成名的理論。海森堡對交談細節的回憶,說明合作學習具有令人吃惊的潛能;集体可以做到比個人更有洞察力、更為聰明。團体的智商可以遠大于個人的智商。
依海森堡所說的這些感想,那么團体學習這項修煉的重要貢獻者之一,竟然是一位當代的物理學家鮑姆,就不足為奇了。鮑姆這位杰出的量子物理學家,發展出“深度匯談”的理論与方法。當一群人進行深度匯談時,他們是以開放的心胸,面對彼此之間一股更大的智識之流。深度匯談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觀念,受到古希腊人的推崇,并被許多諸如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社會加以實踐。然而,深度匯談在現代的世界几乎已經不复存在。其實。許多人都曾領略過深度匯談,這种特殊的交談方式,像是有它自己的生命一般自由發展,帶著我們走上從來不曾想象、也未曾事先計划的方向。但是這樣的体驗難得碰上,因為深度匯談通常都是情境的產物,不是有系統引導与苦心練習的結果。
鮑姆關于深度匯談理論与實踐的近作,將本書前几章所討論的几項修煉背后、兩項主要的智識之流融匯起來:其一是對自然系統性或整体性的看法;其二是思考与內在“模式”之間的互動,以及認知与行動之間的互動。鮑姆說:“雖然有時候在處理較大的系統時非得分割成許多小部分來研究,量子論卻提出,宇宙基本上是整体而不可分割的。就量子理論所要求的嚴謹水准而言,觀察的工具与被觀察的對象,彼此是以一种無法再予分割的方式相互加入。就此一嚴謹水准而言,認知与行動也是如此無法分割的。”
這讓我們回想起前面提過的系統思考關鍵特色:它要我們注意眼前所發生的事情,常是在我們認知引導下的行動所產生的后果。相對論也提出過類似的問題;鮑姆在1965年《狹義相對論》(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一書中也曾經指出過。在這本書中,鮑姆開始更明确地把系統觀點与心智模式連接起來。尤其是他認為科學的目的不是知識的累積(真正的科學家都深切了解,許多科學理論遲早都會被證實是錯的),面是創造、引導和塑造我們認知与行動的“心智圖”,它引導一种“自然与人類意識之間持續的相互加入(mutual Participation)”。
然而,鮑姆最特出的一項貢獻,在于把思維看作是集体的現象,因而對團体學習產生獨到的見解。鮑姆很早就對“電子海”(electron sea)的集体特質,与我們思維運作方式之間的類比感到興趣。稍后,他發現這個類比,對于幫助解釋生命中每一個階段都觀察得到的“思維的反效果”很重要。鮑姆認為;“我們的思維是前后不一致的,而且所造成的反效果是這個世界上問題的根源所在。”他認為思維既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集体的,我們不能只是透過個人加以改善。“我們必須將思維看作是整体現象,起因于我們如何互動以及如何交談。”
深度匯談:觀察自己的思維
交談有兩种主要類型,深度匯談与討論。一個團体如果要能擁有持續開創性學習的能力,這兩种交談都很重要,但是兩者必須配合使用,以產生綜效,才具有威力,然而如果不了解兩者的差异,就無法運用它們產生綜效。
鮑拇指出,“討論”(discussion)這個字跟“碰擊”(Percussion)与“震蕩”(concussion)有相同的字根。它的意象有點像打乒乓球般,將球來回撞擊。一場討論就像是球賽,透過參賽者所提供的許多看法,對共同感到興趣的主題加以分析和解剖。這樣做本來應該有用。然而,一個比賽的目的,通常都是為了要贏;這里所說的贏,是使個人的看法獲得群体的接受。為了強化你自己的看法,你可能偶爾接受別人的部分看法,但是基本上你是想要使自己的看法胜過別人。然而,如果將胜利視為最优先,就無法將前后一致及追求真相視為第一优先。鮑姆認為我們需要一种不同的溝通方式,即“深度匯談”,來改變這种优先順序。
相對于討論,深度匯談源自希腊的dialogos。dia意指“透過”,logos意指“文字”或“意義”。鮑姆認為dialogos之原義是“在人們之間自由流動的意義,就像流蕩在兩岸之間的水流那般”。鮑姆堅認在深度匯談中,群体可以進入一种個人無法單獨進入的、較大的“共同C義的匯集”,它是由整体來架构各個部分,而不是設法將各個部分拼湊成整体。
深度匯談的目的是要超過任何個人的見解,而非贏得對話;如果深度匯談進行得當,人人都是贏家,個人可以獲得獨自無法達到的見解。“如此,以共同意義為基礎的新心智開始呈現,大家不再以反對為主,他們也不能算是在互動,而是加入這個能夠不斷發展与改變的共同意義的匯集。”
在深度匯談時,大家以多樣的觀點探討复雜的難題,每個人攤出心中的假設,并自由交換他們的想法。在一种無拘無束的探索中,人人將深藏的經驗与想法完全浮現出來,而超過他們各自的想法。
鮑姆認為:“深度匯談的目的,在于揭露我們思維的不一致性,這种不一致的起因有三:一、思維拒絕周遭任何交流加入;二、思維停止追求真相,而像已設定好的程式,下了指令便不假思索地進行;三、思維所面對的問題,正源自它處理問題的方式和模式。”
為了說明起見,試以偏見為例。一個人一旦開始對某一類人有刻板印象,這個想法就變成你行動的代理人,影響自己和這類人接触時的行為。然后對方的行為也會被你這种態度所影響。持有偏見的人,看不見偏見如何影響自己的所見和言行;如果看得見,那也就不是偏見了。偏見在思維運作的時候,總是無法被偏見的持有者察覺的。
鮑姆曾將思維比擬成演戲:“思維總是代我們在前台表演,卻又假裝并不代表我們,它就像演員般,在舞台上演得渾然忘卻他真實世界的角色。我們陷入思維的戲劇之中而不自知。所以每當我們開始思維,就會產生不一致性,因為真實世界已在轉變而戲卻照舊演下去。我們在戲中運作,定義問題,采取行動,‘解決’問題,然而卻与所源出的周遭真實世界失去了聯系。”
深度匯談便是一种幫助人們看清思維“代表”(representative)与“加入”(participatory)這兩种本質的交談方式,使我們對思維的不一致性更敏感,和減少面對思維不一致時的不安。在深度匯談中,人們變成自己思維的觀察者。
我們可由深度匯談中觀察到思維是主動的。譬如在深度匯談中,當沖突被攤出來時,我們很可能會感受到一种緊張狀態,但是嚴格說來,緊張狀態的來源是我們的思維。大家會說:“事實上,沖突源自于我們的思維以及我們執著的方式,而不是源自于我們自身。”一旦看清思維“主動加入”的本質,大家便會開始將自己与思維分解,而對自己的思維采取想更具創造性、而較少被動反應的立場。
增進集体思維的敏感度
在深度匯談中的人也開始注意到思維的集体性本質。鮑姆說:“大多數思維的起源都是集体的,周圍的每個人對自己的思維都有程度不同的影響;譬如語言完全是集体性的,如果沒有語言,我們所知道的那些思維不可能存在。”我們所持的大多數假設,來自文化上可被接受的假設之中,很少有人學會真正自己獨立思考。
集体思維是一种過程,像是一個源源不斷的水流,想法則像是浮在水流表面、而被沖上兩岸的葉子,是那個思維過程所產生的結果。我們收集這些葉子,而把它們當作自己的“想法”,因為我們沒看到產生想法的集体思維之流,所以誤以為想法就是自己。
在深度匯談中,人們開始看見在兩岸之間流動的水流。他們開始加入這個可以不斷發展和改變的、共同意義的匯集。鮑姆相信我們平常的思維過程,像是一個“网目很大的网子,只能同住水流中最粗、最大的要素”。而在深度匯談中,一种超乎平日思維的敏感度發展出來,這個敏感度像是一個网目很細的网,能夠搜集思維之流中不易察覺的意義。鮑姆相信這個敏感度存在于真正智力的根部。
因此,依鮑姆的看法,集体學習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對于發揮人類智力的潛能至關重要。透過深度匯談,人們可以互相幫助,覺察彼此思維中不一致的地方,如此集体思維才能愈來愈有默契。我們很難在此為默契下一個簡單的定義,因為它不是和諧、一致、有秩序等所能表達的。
然而,我們的重點不在于強求某种抽象的默契,而是在共同努力增進全体參与者對于所有可能形成的“不一致”的敏感度。矛盾和混亂或許是不一致的必然現象,但是最根本的不一致,還是在我們的思維產生了不是真正想要的后果。
有效的深度匯談
鮑姆認為深度匯談有三項必要的基本條件:
一、所有參与者必須將他們的假設“懸挂”在面前。
二、所有參与者必須視彼此為工作伙伴。
三、必須有一位“輔導者”來掌握深度匯談的精義与架构。
這些條件可以降低彼此間意義流動的阻力,有助于群体內意義的自由流動。就像電路中的阻力會使電流產生熱量,浪費能源,同樣的,群体若以一般的方式運作時,也會像電路那樣浪費能量。深度匯談中會有一种“像超導体內的冷能源般”(在超導体中,由于電阻差不多為零,電流在其中流轉時,只會產生微少的熱量),能夠使本來可能造成意見不和的“熱話題”(可能引起爭議的話題),變成可以討論的主題,甚而變成窺見更深入見解的窗戶。
一、“懸挂”假設
“懸挂”你的假設的意思是,先將自己的假設“懸挂”在面前,以便不斷地接受詢問与觀察。這并不是拋棄、壓制或避免表達我們的假設,更不是指發表意見是一件坏事,或者應當完全消除主觀意識,而是察覺和檢驗我們的假設。如果我們一味為自己的意見辯護,或未察覺自己的假設,或未察覺我們的看法是以假設而非事實為依据,我們就無從懸挂自己的假設。
鮑姆認為一個人一旦堅持“事情就是這樣”,深度匯談就被阻斷。因此深度匯談時,必須非常用心,因為“心智傾向于避免懸挂假設,而采用沒有商量余地及非常肯定的意見,以使我們覺得必須為它辯護。”
以一家高度成功的科技公司最高層管理團体的深度匯談為例,參加的主管都覺得公司內的研發部門与其他單位之間存在很深的歧見;這個歧見是由于該公司自創辦以來,一直重視研究發展。該公司在過去三十年之中,率先推出一連串轟動市場的創新產品,并成為該項產業的標准。產品創新是該公司市場聲望的基礎。因而,即使這個部門間的歧見造成了許多問題,還是沒人有勇气把它提出來談論。該公司長久以來十分珍惜它的技術領先地位,并且賦予具有高度創造能力的工程師,追求自己產品愿景的自主性。
當被要求談論“懸挂所有的假設”時,行銷主管問道:“所有的假設?”“是的,所有假設。”他得到肯定的回答,但是看起來很困惑。在接下來的談話中,行銷主管承認自己心中持有研發部門自視為公司得胜關鍵的假設,并由此他進一步假設這使研發部門漠視可能影響產品發展的市場資訊。研發部門經理這時表示,他也假設別人是這樣看他,而令人意外的,他覺得這個假設限制了研發部門的效能。于是雙方都体認出這些假設全是“假設出來的”,而不是經過驗證的事實。結果,接下來的深度匯談變成很開放,對一些看法進行不同的探討,討論之誠懇和深入是前所未見的。
“懸挂假設”,很像第十章“心智模式”所討論的反思与探詢技巧中所看到的“跳躍式的推論”与“探詢推論背后的論證”。但是在深度匯談中,懸挂假設必須集体去做。團体懸挂假設的修煉,可以讓成員更清楚地看見他們自己的假設,因為此時可以把自己的假設跟別人的假設對照。鮑姆認為懸挂假設是件不容易做好的事情,這是因為思維本質的緣故;思維會不斷的使你深信,事情原本就該如此。團体懸挂假設的修煉,是此种錯覺的解毒劑。
二、視彼此為工作伙伴
團体的成員只有視彼此為工作伙伴,才能共同深入思考問題和發生深度匯談。視彼此為工作伙伴很重要,因為在團体溝通的過程中,彼此的思維會不斷地補足和加強。把彼此視為工作伙伴,能產生較好的互動。這看似簡單,但是它能夠使情況大為改觀。
視彼此為伙伴,對于建立一种成員彼此間關系良好的气氛,以及消除深度匯談時由于階級差距所帶來的障礙有所幫助。因為在深度匯談中,人們确實覺得好像他們是在建立一种新的、更深入的了解。彼此視為伙伴,看似簡單,卻极為重要。我們跟伙伴与非伙伴的交談方式不同。有趣的是,隨著深度匯談的進展,團体成員會發現,甚至跟那些原先与他們沒有多大共同處的人,也發展出伙伴的感覺;其中關鍵在于彼此視為伙伴的意愿。此外,將假設懸挂出來也常令人覺得不安,視彼此為伙伴可以減少這种不安的感覺。
工作伙伴的關系,并不是說需要贊成或持有相同的看法。視彼此為伙伴真正能發揮力量,反而是在看法存有差异的時候。雖然伙伴的感覺,在每個人都贊成的情況下較為容易產生;但如能在意見出現重大不一致的情況下,發展出此种視“反對者”為“意見不同的伙伴”的想法,則收獲更大。
鮑姆認為在組織進行深度匯談是极不容易的,主要是由于組織階層會使伙伴關系難以建立。他說:“階層和深度匯談是背道而馳的,而組織要避開階層結构很困難。”他問道:“那些掌握權力的人真能和部屬平起平坐嗎?”這樣的問題對組織中的團体有几項啟示。第一,每一位參加深度匯談的人,真正想要得到深度匯談好處的意愿,必須高于保持階層优勢的欲望。在組織的深度匯談中,不但要除去因地位高而可能占优勢的情況,同時要避免因地位低而害怕陳述自己看法的情況。深度匯談是极有趣的,但需要有意愿多方探索這些被提出的新构想,并檢驗和測試它們。如果過度關切誰說了什么,或自己的想法是否愚昧可笑,“深度匯談”就不再是有趣的過程了。
懸挂假設及視彼此為伙伴這些條件一定要确實做到。我們發現,在團体中,如果每個人事先知道他在深度匯談中被期望什么,則許多組織中的團体都具有接受這項挑戰的能力。事實上,我們在內心深處都有深度匯談的渴望,特別是在針對最重要課題的時候。但這并不意味在組織內深度匯談總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參加深度匯談的成員,不愿奉行懸挂假設与建立伙伴關系的條件,是不可能做到深度匯談的。
三、掌握深度匯談精義与架构的輔導者
缺乏熟練輔導者的情況下,過去的思維習慣會不斷把我們拉向討論,而拉离深度匯談。尤其是在發展深度匯談成為團体修煉的早期,我們習于將思維所代表的假設視為真相本身,相信自己的想法比別人的更正确,并怯于在眾人面前將自己的假設懸挂出來;至于要將“所有的假設”都懸挂出來,更是令人感到不安。(總是該有一些假設要保留一下吧;否則叫我怎么做人?)
一個深度匯談的輔導者必須做好一個“過程顧問”(process faclltator)的許多基本工作,這包括幫助人們了解他們自己才是過程与結果的“主人”——對深度匯談結果負成敗責任。如果輔導者未能扮演好角色,讓成員感覺某項話題被刻意地禁止,成員便會開始抱著保留的態度,而不愿懸挂假設。輔導者也必須保持對話的進行順暢而有效率。如果有人在不該討論時,開始把過程轉向討論,輔導者要能及時識別并佐正之。更重要的是,輔導者對于進行中的匯談過程,總是小心翼翼地拿捏應該啟發或直接協助,且不以專家的姿態出現,以免有些成員因過份注意輔導者而分散了注意力,或疏忽了自己的想法及責任。
除此之外,輔導者的另一項功能是:基于他對深度匯談的了解,使他可以透過參与去影響深度匯談發展的動向。譬如,在某一個人作了某項觀察与推論之后,輔導者可能提醒大家:相反的情況也可能是對的。也就是說,除了擔任深度匯談的提醒者之外,輔導者的參与也是一种深度匯談的示范。深度匯談的藝術在于体驗其中的意義,也就是看清當下需要說的話。輔導者只在必要的時刻講話,而且做正确的示范,這比任何抽象的說明更能加深他人對深度匯談的体認。
當團体養成了深度匯談的經驗与技能,輔導者的角色漸漸變成不那么重要,或可以成為參与者之一。一旦成員深度匯談的技巧養成了,團体就養成一种沒有領導者的群体。在習于深度匯談的社會中,通常不需要指定輔導者。譬如,許多美國印第安族群,深度匯談的修煉境界便已高達如此;其中巫醫和智者各有他們自己的角色,但是群体能夠靠自己開始進行深度匯談。
交互運用深度匯談与討論
在團体學習之中,討論是深度匯談不可少的搭配。討論是提出不同看法并加以辯護,這可能對整個狀況提供有用的分析。深度匯談則是在提出不同的看法,以發現新看法。通常我們用深度匯談來探究复雜的問題,用討論來作成事情的決議。因此如果團体必須達成協議,并必須作成決定,討論是需要的。在討論之中,大家依据共同意見,一起來分析,以及衡量各种可能的想法,并由其中選擇一個較佳的想法(也許是原來的想法之一,或是從討論中得到的新想法)。如果具有成效,討論將匯集出結論或行動的途徑。相反的,深度匯談是發散性的;它尋求的不是同意,而是更充分掌握复雜的議題。深度匯談和討論都能產生行動的新途徑;如何行動通常是討論的焦點,然而新的行動只是深度匯談的一种副產品。
一個學習型的團体善于交互運用深度匯談与討論。二者的基本規則不同,目標也不同,如果無法加以區別,通常團体就既不能深度匯談,也無法有效地討論。
經常深度匯談的團体,成員之間會逐漸形成一种獨特的關系。雖然這种關系對討論不一定有所幫助,但是他們發展出一种彼此間深深的信任。他們對每一位成員獨特性的觀點,逐漸有了充分的了解。另外,他們体會如何溫和主張自己的看法,而使更廣泛的見解逐決出現。他們也學習如何持有立場,而不被自己的立場所“持有”的藝術。當需要為自己的看法辯護時,他們不會沖動,或固執己見、毫無轉圜的余地,或把贏當作第一要務。
此外,与深度匯談所需的技巧大致相同,探詢与反思(本書第十章“心智模式”所介紹的)也是討論必備的技巧。事實上,深度匯談如此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它提供一個有安全感,又可讓心靈自由發展的環境,使這些技巧得以磨練,并能引發深入的群体學習。
反思、探詢是深度匯談的基礎
在鮑姆的思想中,我們得到了在第十章中所談的“行動科學”方法的回響,即讓個人的想法攤出來接受影響的重要性,以及澄清我們的心智模式与真相混淆的問題。鮑姆的成就之所以不凡,是因為他清晰地描述了一個新的愿景,指出在群体之中一种新的可能,以超越行動科學家所指陳的“無能為力”。此外,鮑拇指出深度匯談是一种團体的修煉,無法由個人達成。
深度匯談的目標之一是,為一個群体匯集更多的意義和想法。這個目標,乍看之下可能顯得有些難于理解,但對于長久以來一直想培養集体探詢与建立共識的管理者而言,是深切需要的。
這些管理者早就學會區別兩种類型的共識:一种是“向下聚焦”型的共識,在各种個人觀點之中找出共同部分:另一种是“向上開展”型的共識,尋找一個比任何個人觀點為大的景象。第一類型共識是以個人觀點的內容為出發點,找出自己与他人看法的共同部分,而建立起大家都同意的共同立場。第二种類型則是一种探究真相的方式,是以每個人都有一個觀點的想法為基礎,來建立更高層的共識。每個人的觀點都是對一個較大真相的獨特視角;如果我們彼此能透過別人的觀點來“向外看”,則每一個人都將多看到些自己原來看不到的事物,而深度匯談有助于形成這种共識。
如果深度匯談明确地成為團体學習的一個特有的愿景,那么反思与探詢的技巧,對于實現這個愿景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個人愿景提供建立共同愿景的基礎,反思与探詢技巧也提供了深度匯談与討論的基礎。建立在反思与探詢技巧上的深度匯談,將是一种更可靠的團体能力,因為它較不依賴如團体成員之間、某种良性關系這類特定的先決條件。
善用沖突
和一般的想法相反,杰出的團体的特性并不是沒有沖突。相反的,就我所知,團体不斷學習的一項可靠的指標,是看得到彼此想法之間的沖突。杰出團体內部的沖突,往往具有建設性。事實上,建立愿景的過程,便是從原本相互沖突的個人愿景之中,逐漸浮現出一個共同愿景。即使當人們已經分享一個共同愿景,對于如何達成愿景,可能仍有許多不同的想法。愿景愈是崇高,我們對于如何達成愿景就愈加不确定,沖突也愈多。當團体中每個成員都苦于無法找到新的對策時,攤開相互間的沖突,讓想法自由交流是很重要的;此時沖突實際上成了深度匯談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平庸團体的內部,通常以下列兩种方式之一來處理沖突: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都沒有沖突存在,就是為极端的見解僵持不下。表面呈現和諧的團体,成員們相信,為了維持團体的完整,必須抑制互相沖突的看法。他們認為,如果每個人都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團体將會被不能凋合的歧見弄得分崩离析。在一個意見极端化的團体中,互相沖突的看法根深蒂固地存在團体里;雖然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的立場是什么,但少有愿意退讓的。
習慣性防衛
阿吉瑞斯和他的同事共花了二十五年以上的時間研究這個困局:為什么聰明而又有能力的管理者,在管理團体之中常無法有效學習。結果他們發現:杰出的團体与平庸的團体之間的差別,在于他們如何面對沖突,和處理隨著沖突而來的防衛。阿吉瑞斯說:“我們的內心好像被設定了習慣性防衛的程式。”
如第十章“心智模式”所述,習慣性防衛是根深蒂固的習性,用來保護自己或他人免于因為我們說出真正的想法而受窘,或感到威脅。習慣性防衛在我們最深層的假設四周形成一層保護的殼,保衛我們免于遭受痛苦,但是也使我們無從知道痛苦的真正原因。然而,根据阿吉瑞斯的研究,習慣性防衛的根源,并不如我們以為的是強詞奪理,或是為了保持社會關系,而是懼怕暴露出我們想法背后的思維。阿吉瑞斯說:“防衛性的心理使我們失去檢討自己想法背后的思維是否正确的机會。”對多數人而言,暴露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法是一种威脅,因為我們害怕別人會發現它的錯誤。且這种認知上的威脅自孩提時便開始,許多人在學校里更是不斷地加重。還記得被點名問問題而沒答對的創傷嗎?在日后工作中,這种情形更加嚴重。
習慣性防衛种類繁多,且常常發生,但通常不會引起注意。當我們無意認真接受某一個想法時,我們會說:“那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构想。”我們故意不斷說服別人某個构想行不通,而真正的想法只是不想再考慮這個构想。或者我們假裝支持他人某項論點,以免讓自己類似的論點也遭到批評。或者在一出現困難議題時,便改變話題,表面上則顯得很有風度、若無其事的樣子。
什么造成組織內的政治游戲?
最近有一位以強勢領導的某公司總裁,向我感歎他的組織內部缺乏真正的領導者。他覺得自己的公司充滿听命行事的人,沒有執意追求愿景的理想家。這對一位自認擅于溝通和勇于承擔風險的領導人來說,尤其感到挫折。事實上,正是因他明确地表達“他的”愿景,以致于他周圍的人感到怯懼;也因此,他的看法很少受到公然的檢視与挑戰。員工已經學會了不在他面前表達自己的看法与愿景。雖然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強勢當作是一個防衛策略,但如果他細心地觀察,應該會看到自己正是如此。最“有效”的習慣性防衛,往往就像那位強勢領導的總裁所使用的,是那些看不見的習慣和思維方式。這位總裁如此行事,自然使自己的看法免于受到挑戰。
在組織中,如果大家認為對事情的了解不夠完整或是不正确,是一种差勁或無能的表征,習慣性防衛所衍生出的問題就更加嚴重。許多組織的管理者有一种心智模式,認為管理者必須知道所發生的任何事情。那些已經晉升到高階的管理者,擅于表現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那些意圖晉升高階主管的人,也很早就學會表現出一副很有自信的樣子。
有這种心智模式的管理者,通常被兩种束縛所捆綁。有些人被這种假裝出來的信心自我蒙蔽了,相信自己知道絕大多數重要問題的答案。為了保護自己這樣的信念,他們必須自絕于其他可能看法,使自己不受影響,以堅持既定的立場。另一种人則相信他們被期望知道是什么造成問題,但是在內心深處對自己的解決辦法并沒有把握。這一种束縛是隱匿自己的無知,維持看起來有信心的樣子。不論是屬干哪一种束縛,管理者都會因此養成習慣性防衛,絕不顯露自己決策背后的心理,以維持他們是個有能力的決策者風采。
這樣的防衛心態變成組織文化中可以被接受的一部分。阿吉瑞斯說:“我曾經問過,是什么造成組織內的政治游戲?答案是人性与組織特性。我們是習慣性防衛的帶原者,組織是我們的寄身處。一旦組織也被感染了,它們也成了帶原者。”
團体是大組織中的一個小世界,因此大組織所顯現的防衛特性也深植于團体之中,這并不令人惊訝。事實上,習慣性防衛阻礙了本來可以貢獻于共同愿景的團体能量。對于陷入習慣性的防衛的團体成員而言,他們覺得好像碰上了許多隱形的牆和陷阱,完全無法共同學習,如圖12—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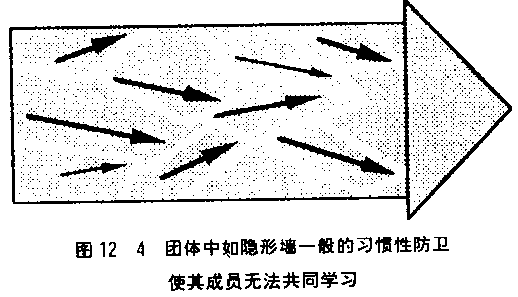 |
組織中的隱形牆
為了体認團体習慣性防衛的影響是如何重大,這里以某公司成立不久的部門ATP產品的真實個案為例。這是一家具創新性、高度分權的公司。泰德年方33歲,為該事業部門總經理,對公司的“自由”与“地方自主經營”這兩項价值觀深信不疑,且篤實力行。他對本部門的ATP產品有強烈的信心;該產品是以新的印刷電路板技術為基礎發展出來的。他非常熱心,是員工當然的拉拉隊長。因而他的管理團体成員工作格外努力,分享他對ATP前景的熱忱。
他們的努力得到回報,訂貨連續几年快速成長,1984年銷售達2O00万美元。如此快速成長的原因,是兩家主要的迷你型電腦制造厂商對此公司的技術深具信心,因此將該公司的電路板納入他們硬体新產品線的設計,并大量生產。但是,1985年在迷你型電腦產業不景气的打擊下,這兩家制造厂商暫停此新產品的生產,使該公司預估的訂貨減少50%。1986年景气并未回升。泰德終于被解除部門總經理的職務,重任工程主管。
這家公司出了什么問題呢?問題在于管理者一方面對自己的產品深具信心,另一方面卻為了取悅總公司,而設定了一個在內部并不能完整搭配的積极成長目標,銷售人員因此產生了很大的業務壓力。為了纖解壓力,銷售人員以和少數几家關鍵客戶建立大量而急速的交易作為因應,因此對這些客戶的依賴日深。當這些客戶有几家碰到營業問題時,該公司也就難逃劫數了。
為什么這個部門的管理團体核准讓這個風險极高的策略執行?為什么總公司的領導階層不介入,建議這位年輕的事業部l‘了主管分散他們的客戶群?他們問題的核心是深藏在一個“舍本逐末”結构中的習慣性防衛,如圖12—5所示。
 |
如阿吉瑞斯所說,習慣性防衛是對一項問題的反應;這里問題被定義為“已經知道的”和“需要知道的”兩者之間的“學習差距”。彌補此項差距的“根本解”是探詢,因為它能逐漸導致新理解与新行為,也就是學習。但是學習新事物對某些成員而言是一种威脅,因此個人与團体會對威脅作出防衛性的反應;這便導致“症狀解”:用習慣性防衛來降低認知上的學習需求,以消除學習差距。
泰德和ATP其他管理者都被他們自己特有的習慣性防衛束縛住了。有几位管理者曾經表達他們對依賴少數几家大客戶的擔憂。當這項問題在會議上提出的時候,每個人都同意那是一項問題,但沒有人對這項問題采取任何行動,因為每個人都太忙了。由于泰德對ATP產品有著無比的信心,所訂定的成長目標又深具挑戰性,使管理者產生了強大的業績壓力,他們積极擴大產能,這又產生不斷接新訂單的壓力,而顧不得這些新訂單從哪里來的。
總公司主管也被一個類似的束縛綁住了。總公司也關切ATP的客戶群太過狹窄,有些總公司主管私下質疑泰德的計划并不能提升公司長遠經營的能力。但是這些主管既不愿破坏公司向來尊重部門總經理經營權限的价值觀,同時也不愿使泰德難堪,所以他們只作間接的批評或保持緘默。
泰德也曾對自己的方案感到猶疑不定。他以前不曾擔任過事業部門總經理的高階職務,很渴望這次能證明自己的才能。由于不愿讓部屬和上司們失望,所以他絕口不談自己對設定積极成長目標的不安。
這些存在于ATP其它管理者、總公司与泰德心中的困扰与矛盾,被掩蓋在習慣性防衛之下,因而從未獲得化解。ATP的管理團体礙于泰德對于成長目標的熱切,始終未采取應有的行動。總公司的管理者礙于公司的价值觀,也始終未能對泰德提出應有的忠告。泰德則是雖需要幫助,但是又不想顯得沒有自信的樣子。以該公司強調的互相支援、同志愛及一体的精神,這些困扰原本應該有許多處理的方式,但卻受困于習慣性防衛這個組織中的隱形牆。說實話的恐懼
習慣性防衛愈是“有效”,背后的問題就愈不易彰顯,問題也因此得不到有效的解決,這使得原本就發發可危的情況,更加惡化。這是因為他們并未運用學習來解決根本問題。在這個例子中,由于他們沒有采取真正的對策——如何擴大客戶群,問題因而更加惡化。就像所有舍本逐末的結构一般,團体愈是訴諸習慣性防衛,就變得愈加依賴它們。阿吉瑞斯指出,當習慣性防衛成功地消除了眼前的痛苦,它們也同時阻礙我們獲悉怎樣消除造成痛苦的根源。
阿吉瑞斯又說,習慣性防衛常被人刻意地隱藏起來。這是因為一般的輿論都贊成開放,而認為防衛是不好的,使大家不愿意承認自己有習慣性防衛的心態。如果泰德的總公司主管曾經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是為了避免引起沖突与尷尬,所以未曾當面指出泰德計划的缺失,他們必然已經避免了這個想法。同樣的,如果泰德能說出:“我是在逃避使自己看起來軟弱無能”,他的防衛策略將不會持續太久。但是沒有人說出這些感覺,因為說出事實的恐懼使每個人一開始就采取習慣性防衛。
如何降低習慣性防衛?
用什么方法可以降低習慣性防衛呢?多數“舍本逐末”結构,杠杆點所在位置有兩個可能的方向:一、削弱症狀解,二、增強根本解。削弱症狀解
削弱症狀解的方法之一,是先行減低防衛反應對情緒上的威脅。譬如,如果泰德對于在總公司上級主管面前坦然承認他自己沒有把握,或上級主管們對泰德坦然說出他們心中的疑問,這樣在發生習慣性防衛的時候就處理它們,便可以削弱症狀解。習慣性防衛只有在禁止討論的環境中才會強而有力;或只有當團体假裝自己沒有習慣性防衛,像鴕鳥般對問題視而不見,才會受困于習慣性防衛,一旦開放討論,它們就會“見光死”。
但是如何使問題變得可以被討論,是一項巨大的挑戰。嘗試“治療”別人的習慣性防衛,几乎一定會受到還擊。例如,質問某個人為什么表現出防衛的行為;几乎毫無例外的,對方的第一個反應是抗議:“我?我并沒有防衛的行為!”而向別人提出此問題者,似乎并不了解如此的問法反而只會加強對方習慣性的防衛。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我們認為別人有習慣性防衛心態在作怪,极可能我們是這個習慣性防衛互動結构的一部分。有技巧的管理者知道如何處理防衛、而不會導致更加防衛的情況。
他們的做法是自我揭露,并以詢問的方式探究自己和別人防衛的原因。例如,他們可以這樣說:“我覺得這個新提議不妥。你或許也有這种感覺,能否幫我看看這個不妥的感覺來自何處?”或“我所說的合理嗎?我的溝通方式是否太過強硬或主觀?但是我想听听你的觀點,這樣我們可以對狀況有一個更加客觀的看法。”這兩段話都承認講話的人感到不妥,而邀請別人一起探詢原因。增強根本解
消除習慣性防衛所需的技巧,基本上与在“舍本逐末”結构中增強“根本解”的技巧是相同的,也就是反思与相互探詢的技巧。以探詢的方式討論問題的原因時,個人應毫不隱藏地攤出自己的假設和背后的推理過程,并鼓勵別人也如此做。如此一來,習慣性防衛便無從發生作用。
雖然習慣性防衛對團体特別有害,然而,如果真正有學習的決心,團体正是轉化個人習慣性防衛的最佳場所。所需要的,正是前面再三提出的,是一個我們真正想要的愿景,其中包括企業的績效、希望如何在一起工作,以及坦誠地說出“目前狀況”真相的決心。在這個意義下,團体學習与建立共同愿景是一体兩面的修煉。這兩項修煉自然可結合形成團体的創造性張力。
在真正共同愿景的面前,習慣性防衛變成只是目前現況的另一個面向。就像在“自我超越”一章所談的,結构性沖突之所以會危害個人或組織成長,是因未被察覺。一個忠于真相的團体,有勇气承認自己的習慣性防衛,則習慣性防衛就開始成為一种動力的來源,而非阻力。
它的做法是,如果我們將習慣性防衛當成一种團体學習停滯了的信號,那么習慣性防衛也可成為在建立學習型團体的過程中一個親密的戰友。當我們是在防衛的時候,縱使我們無法充分斷定防衛的來源或模式,多數人還是覺察得到。學習型團体的實用技巧可以用于辨認下列的問題:別人是否對自己的假設加以反思?是否探詢彼此的思考?是否先攤出自己的想法以鼓勵他人探詢自己的想法?當我們感覺自己在防衛、逃避問題,或思考如何保護某人或自己,表示我們應該重新努力學習的時候到了。但是我們必須學習如何辨認這些訊號,和學習如何承認防衛而不會激起更多的防衛。
習慣性防衛的強弱,可能是問題的困難度与重要性的指標。防衛的強度愈高,問題往往也愈重要。習慣性防衛如果處理得當的話,它可以為彼此的思考開一扇窗。當團体能夠以“自我揭露”和“兼顧探詢与辯護”成功地處理防衛時,團体的成員就開始更加看清彼此的思考。
最后,當團体成員學會如何運用、而不是排斥自己的習慣性防衛,他們建立了處理自己防衛心態的信心。習慣性防衛使成員受困,并損耗他們的心神和精力。所以當團体成員超越了妨礙學習的障礙——這些被許多人認為是無可避免的、甚至是組織本質的障礙——之后,他們獲得一种實際的經驗:也許現況中的許多其它問題,他們也是有力量加以改變的。
學習型團体的煉全術
在中古時代流行的煉金術,是嘗試把最普通的鉛,變成最珍貴的黃金。學習型團体也是在演練一种特殊的煉金術,把具有潛在分裂作用的沖突与防衛變成學習。他們透過自己的愿景与技巧來試煉。并透過深度匯談,成員得以真正体認范圍更廣、可產生巨大作用的團体智慧和共同愿景。除此之外,團体也需看清現況的真相,他們的學習能力才得以更扎實。當然,反思与探詢的技巧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為當防衛出現的時候,他們是否能繼續以學習來改善問題,將視是否有此技巧而定,否則他們還是會故態复萌。
一個能夠學習的團体所表現的特征,并非沒有防衛,而在于面對防衛的方式。一個下定決心學習的團体,不僅必須承諾要忠實地敘述外面的情況,在面對本身內部所發生的事時,一樣要說實話。為了進一步看清真相,我們還必須看清自己用來遮蓋真相的策略。
當修煉到相當程度的時候,能量与洞察力開始顯現。習慣性防衛實際上就像一座保險箱,過去我們把集体學習的能量鎖在里面。現在,經由修煉,這座保險箱的鎖被打開了,洞察力与能量被釋放出來,可用來建立共識,并且朝向團体成員真正想創造的事情推進。
虛擬世界的演練
團体學習是一种屬于團体的技巧,無論再努力都無法單獨學習。一群富才干的學習者,未必能夠成為一個學習團体,好比一群有天分的運動員,未必能成就一個杰出的運動隊伍一樣。在學習型團体中,人人都在學習如何共同學習。
團体技巧的養成,比個人技巧的養成更具挑戰性。這是為什么學習型團体需要“演練場所”和練習方式,來讓他們發展集体學習的技巧。缺乏有效的演練,或許是大部分的管理團体無法成為有效學習單位的主因。
“演練”到底是什么?熊恩在他的《反思的實行者》(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一書中,把他所認定的重要演練原則,比喻為在一個“虛擬世界”(virtual world)之中做實驗。虛擬世界是一個“依真實世界所建构的表征”,它可能像建筑師的素描簿那么簡單:在這上面,他們可以畫圖,以空間語言談論他們的提議,留下建筑物式樣的藍圖。因為圖畫可顯示出最初憑空想象時,沒有預測到的問題,具有實驗的功能。
虛擬世界的精神,在于它容許有實驗的自由。行動的步調可以放慢或加快。在真實世界發生速度很快的現象,在這里可以放慢來看,仔細地加以研究。原本時間拉得很長的現象,在此可以“壓縮”,以更清楚地看見某項行動的后果。在虛擬世界中,沒有不可逆行的行動。在真實情況中不能逆轉或重作的行動,在此可以無限次重來。環境中的改變在此可以完全或部分被消除。复雜的現象可以經由整理在真實世界中糾纏不清的變數而予以簡化。
熊恩所描寫的建筑師及其他專業人士對于虛擬世界的熟練的操控,与籃球隊或交響樂團演練的情形十分相像。他們變化行動的步調,譬如放慢音樂或以慢動作進行比賽。他們分离各個构成部分,并簡化复雜性;譬如分開演奏各個小節,或在沒有對手球隊的情形下進行比賽。或可重复演練,譬如一再重复演奏同一個小節,或一場又一場的練習比賽。
有趣的是,企業團体中少數几個能長時間在一起不停學習的例子,似乎正好都是以有效的虛擬世界來運作的。例如,現代廣告的運作便是以一個富創意團体的概念為基礎,即專案負責人、廣告設計、与廣告撰文三者在工作上密切配合,集思廣益,而創造出新构想。他們往往是一做好几年。這些團体的配合如此密切,最后常常發生隊友一起跳槽到別家廣告公司,而非各奔前程。廣告團体之所以特別,是他們在一起演練的一貫性与密集性跟籃球隊成員沒有兩樣。他們共同激蕩腦力去构想,然后實驗這些构想,以情節板(storyboard)或模擬場景不斷測試,最后提出簡報——先向上級簡報,然后再向客戶簡報。
團体學習要定期有這類演練。但是目前的管理團体通常欠缺這樣的演練。他們對于各种构想确實有過概念性的辯論,也很了解彼此的意見。但是缺少類似情節板或排演的動作。企業團体的主要工作成果,是針對特定的狀況(往往在很大的時間壓力下)進行辯論和作出決策,而且每一個決策一經作成就是最后決定;并未對決策進行實驗,也很少有机會對其他解決方案再加評估,或再回頭以團体的方式反思如何能共同達成更佳決策。
學習如何“演練”
我相信團体學習的修煉在今天已經具備突破的條件,因為我們已漸漸學會如何“演練”。特別是,有兩种不同的“演練場”正在發展中。第一种是在團体中練習深度匯談,以結合眾人的智慧,使團体智商高于個人智商。第二种是建立“學習實驗室”(learning laboratory)与“微世界”(microworld),在電腦支援的環境中,團体可學習面對复雜企業狀況的動態,我們將在第十八章介紹這种演練場。
深度匯談的集會可以讓團体聚在一起“演練”匯談,以及發展它所需要的技巧。這樣一個集會包括下列基本條件:
一、把“團体”所有的成員集合起來(這里“團体”指彼此需要,并一起行動的一群人)。
二、說明深度匯談的基本規則。
三、厲行這些基本規則,以便在有人發現無法“懸挂”自己的假設時,團体可辨認出現在進行的是“討論”,而不是“深度匯談”。
四、誠懇鼓勵團体成員提出最困難、敏感、具沖突性、而對團体工作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把深度匯談集會看作“演練”,因為它們的設計是用來培養團体技能。這樣的集會產生的結果是极為重要的。
前不久,美國電腦資訊公司(Data Quest Drives,一家磁碟机与電腦周邊設備制造厂商)的管理團体曾舉行過一次深度匯談集會。前面曾經提過這家公司素有科技創新之良好市場形象。但這家公司內部最近有了些改變;除了改由研發部門帶頭以外,此公司深具魅力的創辦人,在領導公司成長三十多年以后,最近退休了。新的管理團体在第一年時勉強維持業務成功,之后情況便開始坎坷。新任總裁麥卡錫(John Mac-Carthy),除了面對秉承前人傳奇性成功這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挑戰,還要面對更為艱苦的業務狀況(市場整体已經供過于求),以及在工作上還未凝成共識的工作伙伴。
混亂的改組才告复原,管理團体接到總裁麥卡錫的信函,邀請他們參加一個為期兩天的聚會,信函內容如下:
備忘錄
發文:約翰·麥卡錫
主題:特別會議
我想大家都充分了解,目前公司正在加快改變的速度,在我們的策略与執行計划定案之前,我需要听取你們的意見。我相信還有机會讓我們增進彼此的了解和推動變革的方式。
這次聚會的安排,先是進行一系列的深度匯談,幫助我們厘清執行關鍵策略背后的假設、方案与責任。我們有一個看法,認為只有透過大家的集思廣益,在執行變革計划時,才能步調一致,而不會有含糊不清的地方。這兩天聚會的目的,是徹底思考此刻我們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以了解彼此的看法。
這個聚會与其說是企圖作出決定,不如說是一個檢驗這些決定背后方向与假設的安排。我們還有另一個目標,就是大家在一起視彼此為工作伙伴,把所有的角色与職位棄之門外;在這次深度匯談中,我們應該平等相待,視大家都是對彼此所考慮的狀況有相當了解的人。我們把這次集會看作在我們之間建立持續深度匯談的第一步。我們的經驗已經顯示,從事深度匯談需要演練,我們應當期待從這次的聚會中學習如何練習。以下几項基本規則是很有幫助的,我們邀請你盡最大可能在深度匯談中應用這些規則。
建議的基本規則
一、懸挂假設:基本上我們往往只采取一個立場,并保衛、堅持這個立場。其他不同意的人則站在相反的立場,結果是產生意見兩极化。在這個聚會里面,我們所想要的,是檢驗在我們的方向与策略背后的假設,而不是尋求保衛這些假設。
二、視彼此為工作伙伴:我們要求每一個人把他的職位棄之門外。這次的集會是不分等級的,但是輔導者是一個較特別的角色,他使我們的匯談循正确的軌道進行下去。
三、探詢的精神:我們希望大家探索自己看法背后的思考,也就是自己可能持有的更深層假設,以及導致他們產生這些看法的證据。所以不妨以這樣的問題開始探詢:“是什么導致你說出或相信這個?”或“是什么使你問起這件事情?”
在這兩天的期間,許多以前鎖在心中的問題被釋放出來了,溝通的障礙降低了,不和也痊愈了。更重要的是,研發部門与行銷部門兩單位之間的關系因而改善。
研發主管喬伊与行銷主管查理,兩個人維持友善卻保持距离的關系已經有十年多。兩個人對此公司的成就深感自豪,并對該公司“參与式管理”(Partlclpatlve manasement)及對人与組織的理想,有高度的認同和承諾。然而,兩人陷入一种難以自拔的沖突之中,這种沖突壓制了該公司磁碟机持續成長的力量。研發部門被看作藝術家、設計家和創造者。行銷則被認為(甚至自己認為)是次一等員工,必須在混亂中跟各地設備老舊又斤斤計較的經銷商以及憤怒的顧客打交道。
研發与行銷兩种不同的文化,反映在公司的許多沖突之中。譬如,喬伊和查理各有他們自己的產品預算;前者的預算用來開發新產品,后者的預算用來購并一些規模較小的公司,以補足該公司產品線的產品,并且使公司在市場上更有競爭力。然而沒有整体的計划來統合這兩個單位。行銷部門覺得研發部門對整体的客戶需求未能适時反應,而負責与客戶直接接触的行銷部門,卻要收拾殘局。研發部門卻認為自已被排除在重要的產品計划決策之外。然而當深度匯談逐漸展開后,喬伊急切的建言讓大家吃了一惊,因為大家都假設研發部門十分重視它的自主性。
喬伊:我想提供一個怎樣看產品策略的方式。我今天提出的這個產品策略可看作比腕力。實際上我們已經演變成一個雙頭產品策略,而從未有人公開指陳過。形成這雙頭政策的原因,是我們并未真正把組織內各方面的人集合起來,一起去了解我們的產品到底在自制与購買上應有怎樣的比例分配。一批人把錢花在甲項產品計划上,而另一批人因觀點不同,把錢花在乙項產品計划上。這個雙頭政策總是沒有合而為一的時候。事實上,應該有一個統合研發与行銷兩方意見的上層產品策略。在這個產品策略之下制定自制或購買的決策。
麥卡錫:我想我們基本上都贊同這個看法。
喬伊:我可以再說嗎?
其他人:當然。
喬伊:事實上我們現在是在反其道而行,這比做得不夠好遠要嚴重。
查理:在決定自制与購買比例時,我也曾不斷重复思考這個問題。它出現不協調的原因,是我們一方面把焦點放在解決問題,即由研究帶動的策略,在另一方面,對于公司沒有生產的產品,我們又透過購買其他工厂的產品來補足產品种類。之所以會有購買其他工厂產品的決定,是因為這比研發導向的政策更能回應市場反應。另一個原因是,我們想要研究工作保持單純。
菲力普(人力資源副總裁):我想這是使我們陷入沖突的原因。
喬伊:絕對沒有錯!那就是問題,就是我無法容忍的偏見。請不要借口是在保持研究工作的單純。
查理:唉……我只是坦白說出我們确實這么想。也許還有更好的方式去做這件事情。但是我确實這么認為:在過去有几次我們決定不在研發上面投資目前市場流行的普遍机型,因為那不是創新的。我們想把有限的資源与才能分配在公司的市場形象上面,那就是研究、創新、產品領導……所以我們才向外面買普遍的机型。
菲力普:讓我們今天打開天窗說亮話。我可以告訴你們什么總是困惑我,讓我夾在行銷和研發兩個單位間難以自處。我們總是將自己定位成“由研發帶動產品的公司”。當我們給自己這樣定位時,我們有點是說任何產品,要是沒有本公司投資在創新性的研究,就不是本公司的產品。不管怎么樣,我們已經用那個方式架构自己……。
麥卡錫:那是以研究為基礎的定義方式之一。你是否知道另一個定義方式?就是如果不是新產品,本公司沒有人會對其進行研究發展。
喬伊:我也不喜歡那樣。
菲力普:你說對了!無論我們在董事會上主張要有上層策略方向也好,決定是自制或購買也好,仍然必須是由研究發展帶動的;因為公司的政策就是創新。
麥卡錫:我想我們討論到了一些重點了。我們前面所說的是本公司過去被鎖在一個觀念里,認為能夠使我們出色的只有產品的研究發展,這造成內部很大的緊張關系。我想喬伊幫助我們認清,基本上我們應該提供客戶需要的任何產品。我建議我們可自購買子公司開始,讓公司起步。但還有一种說法認為:“一旦是本公司研究的產品,就必挂上本公司的商標。”然而這种說法并不表示,不是出自本公司研發單位的產品,就不能挂上本公司的商標。要挂上什么標簽應該是一個行銷決定,視你嘗試的定位是什么而定。那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一項不准備挂公司商標的產品,你根本就不會考慮開發。
哈德里(制造部門副總經理):但是那也是在宣示全公司都是由研究帶動的,不僅是研發部門帶動的,包括可能出自公司的其他部門的創新构想,并非全部都透過研發部門。
喬伊:那很好,我不明白為什么這還用說。但是這里面還有一件令我困扰的事情,不知道你們能不能幫我想想看。我覺得自己好像被套上馬鞍,必須代表本公司研發部門過去的傳承。我一直無法接受這點。我發現我愈是拼命把公司向前推進到新的境界,你們就愈想把我們拉回原地!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兩難的困局。
哈德里:同樣的,其它部門的人也有這种感覺。
所有的人:是啊。
哈德里:我們也嘗試把本公司往前推進,但似乎又被拉回原地,因為“除非透過研發部門,否則不算是研究導向和創新。”這個說法把我們困住了。
喬伊:我從來沒說過那樣的話……現在,我可否換個方式來說?我認為我們是一家研究導向的產品公司,這項宣示是正确的。我堅信本公司的成功,部分取決于高超的產品技術。看到任何開始侵蝕這個方針的事情都讓我惊恐。我們必須有好的服務与產品,但這并不表示得到好產品只有一种方式。我們缺乏一個配合良好且同心協力的流程,我們必須建立這樣的流程。
麥卡錫:現在或許我們應有另一种想法:我相信查理在市場和配銷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發展本公司獨家經銷商的新网絡),跟研發部門所進行的一樣重要。
喬伊:我完全相信。
麥卡錫:所以現在令我們困扰的是,如果所作的投資不能即刻得到回收,這個單位就招致嚴厲的批評。
喬伊:歡迎光臨研發的世界(研發的投資都是無法立即回收的)。
查理:從這里我想提出兩點看法。在我看來,有些我們委托外面厂商制造的產品也可考慮是否由你們來發展;而有些由你們發展的產品則可考慮是否授權其他公司制造,以免浪費本公司的研發資源。我始終認為毫無彈性的自制或外包,与商標政策是不合理的。
喬伊:我很同意這個看法……。
查理:還有一點就是在我們的行銷与研發部門之間,沒有有效的溝通方式。事實上,兩個部門愈來愈疏遠。如果我們想要朝向滿足顧客需要的方向努力,必須有一种方式讓這個訊息在公司各角落都被看見。
哈德里:你剛才詢問為什么在研發与行銷之間存在緊張關系?事實上,在制造与財務之間也存在緊張關系。我認為這些緊張關系部分源于組織的控制結构。我今天最大的收獲是,原來并不只是我們這個部門有這种感覺,原來大家都是在類似的處境。整体而言,我們的組織偏向以控制為導向,由上面在控制,我似乎難以插手,這讓我在過去有很大的無力感。現在我准備跳過他們來好好地做些事。
這次深度匯談的結果對電腦資訊公司來說是非常有收獲的。首先,研發与行銷之間長達三十年的不和開始痊愈。其次,行銷部門不再需要單打獨斗地去擴充產品系列,因為研發部門對此也感興趣,并想要加入購并的研究,以及開發不是挂該公司商標的產品,成為搭配產品計划的一部分。神圣不可侵犯的該公司商標,不再限于用自己研發部門開發的產品,而是基于市場考量加以使用。研發部門的最高主管跳脫出該部門獨自負責創新的舊有刻板印象。照他的看法,其他單位都是應該平等對待的創新伙伴,不論是在制程創新、在了解客戶需要,以及在企業管理,都是如此。
團体學習与系統思考
系統思考的觀點和工具對團体學習极為重要。
鮑姆在深度匯談方面的著述,處處透露著整体觀點的訊息。事實上,一條貫穿鮑姆著述的縱軸,是進一步闡揚物理學“整体性”(wholeness)的觀點。鮑姆對當代思潮對集体思考的污染,批評最甚的是“分割”(fragmentation),也就是把事情分解開來的思想趨勢。
學習型團体以整体的觀點來處理習慣性防衛。一般總把防衛看作是別人行為造成的,然而其杠杆點應在于辨認習慣性防衛是共同造成的,并找出自己在產生和持續習慣性防衛時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我們只“在外面”找尋習慣性防衛,而未能看清它們是“在里面”,那么我們愈是努力對付它們,只會愈激起更強烈的防衛。
系統思考的工具對團体學習也同樣重要,因為管理團体的每一項主要工作,如發展策略、塑造愿景、設計政策与組織結构等,實際上都需要克服無比的复雜性。此外,這個复雜性并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不斷在改變。
或許管理團体最大的一項障礙,是他們使用本來只是為了很簡單的靜態問題而設計的“語言”,來應付复雜、動態的實際情況。對此,管理顧問基佛說:“企業的實際狀況是由多個同時發生、相互依存的‘因—果—因’關系构成的。一般語言從這個實際狀況抽离出簡單、直接的因果關系。這是為什么管理者老是往杠杆作用低的方向尋求對策。”例如,如果問題是產品研發的時間太長,我們就雇更多的工程師來縮短時間;如果問題是利潤低,我們就降低成本;如果問題是市場占有率下降,我們就削价來提高市場占有率。
因為我們以簡單而明顯的方式來看這個世界,造成我們深信簡單、立竿見影的解決辦法,而汲汲于找尋簡單的對策,占用了許多管理者的時間。福特阿爾發專案(Project Aloha)的負責人馬諾吉安(John Manoogian)說:“這种發現問題与找出對策的心智,造成必須使用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的短期對策,看起來好像使問題消失了,但是問題事實上卻一再回來。”
管理團体因為集合各种机能,一旦發生這种問題,情況便更加嚴重。團体中的每一位成員都有他自己習用的直線式心智模式,而每個人的心智模式都只專注于系統的不同部分,每個人都強調不同的因果鏈。因此在一般的交談之中,共有的系統圖象不可能以整体顯現,所以討論出來的策略常是七折八扣之后的妥協,且以晦暗不明的假設為基礎,充滿內在的矛盾。如此的策略如何能讓組織中其他的人了解?更不用說如何加以執行了。團体的成員真像是在摸象的盲人,每一個人都知道他摸到的部分,每一個人都相信整只大象必定看起來像自己所接触到的部分那樣,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了解才是正确的。
除非團体共有一种可供描述复雜性的新語言,否則這樣的情況不可能獲得改善。今天,企業惟一的共同語言是財務會計。但是會計是用來處理細節性的复雜,而不是用來處理動態性的复雜。它提供企業財務狀況的片段,卻未說明財務狀況是如何產生的。今天,雖然有一些工具与架构,提供在傳統會計這項語言以外的選擇,包括競爭分析、全面品質与情境企划(由殼牌石油公司所發展而應用,尚未普及),但是這些工具都無法處理動態性复雜。
系統基模的運用
系統基模為管理團体提供了一种有效處理复雜性語言的堅實基礎。例如泰德公司ATP團体如果精于運用基模,他們的交談自然將轉向背后的結构,將愈來愈不受緊急事件和短期對策的左右,并進而看出他們那种狹隘的、只專注于達成每月及每季的銷售目標,將來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特別是如果他們能体會出自己行為中“舍本逐末”的結构:逃避開發新客戶的根本解,而采風險較低的、銷售更多產品給現有客戶的症狀解,將導致更加依賴少數几家客戶。
如果該公司管理者同樣能夠看清楚和討論這個結构,應當能夠更有效地提出他們對泰德管理方法的關切,而不是掙扎著要如何提出不表支持、卻不傷害泰德的看法。他們只需畫出兩個回饋環,彼此相互探詢誰有辦法更有信心地使擴大客戶群這個根本解得到充分的注意。
當這些系統基模被用來討論复雜和有潛在沖突的管理問題時,總是能夠使交談更客觀,談問題的“結构”,也就是產生影響的那些整体的力量,而不是談個性与領導風格。原本難以啟齒的問題,能夠以不帶影射管理無能,或隱含批評的方式提出來。大家會問:“是不是把擔子從擴大客戶群,轉到對現有客戶的銷售?”“如果是這樣,我們怎么知道?”當然,這正是為复雜性而設計的語言帶來的好處,它能客觀而不情緒化地討論复雜問題。
如果沒有一种共同的語言來處理复雜性,團体學習是有限的。如果團体中只有一位成員比其他成員更有系統地看問題,此人的洞識將很難被接受。只因為其他的成員是以我們日常習用的直線式語言來思考,根本無法看到整体的關系。
所以如果團体中的成員都能精熟系統基模語言,則效果非凡;而以團体的方式來學習這种語言,學習的困難度也确可降低。如鮑姆所說的,語言是集体的。學習一种新語言的意思就是學習如何使用此种語言彼此交談。學習一种語言,沒有比使用它更有效的方式。團体開始學習系統思考語言的情形,也是如此。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前一頁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