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頁
回目錄
早晨十點整,奎因警官和他儿子打開了結了霜的玻璃門,上面寫著:
蒙特·費爾德
律師
他們走進了一間巨大的會客室。它的裝飾風格也許可以從費爾德這樣一個男人對于衣服的興趣上找到。里面沒有人在。老警官奎因困惑地看了看,推開門,埃勒里跟在后邊,進了主辦公室。這是間擺滿桌子的長辦公室,除了几排放滿了冗長的法律大本書的書架之外,与報上的“城市之屋”很相似。
辦公室處于劇烈變動的狀態。速記員們三三兩兩湊在一起興奮地喋喋不休;几名男辦事員在一個角落里竊竊私語;房間中間站著赫塞偵探,正認真地跟一個鬢角灰白、表情陰沉的瘦子說話。顯然律師之死在他辦公的地方引起了某种騷動。
奎因父子一進去,辦公室的職員們詫异地你看我我看你,然后一個個伏到桌子上,出現了令人尷尬的冷場。赫塞快步迎上前,他的眼睛布滿血絲,疲憊不堪。
“早上好,赫塞,”老警官簡單地說道,“費爾德的私人辦公室在哪里?”
偵探領他們穿過這個房間到了另一扇門前,門心板上用大大的字母寫著“私人”。三個男人走進一間小辦公室,极為舒适。
“這家伙很有情調,對嗎?”埃勒里格格笑道,坐進了一張紅色皮扶手椅里。
“說說情況,赫塞,”老警官說道,也像埃勒里那樣坐在扶手椅里。
赫塞開始快快地講。“昨晚到了這里發現門鎖著,里面沒有一絲光的跡像。我貼得很近听了听,但是什么也听不見,所以我理所當然地認為里面沒有一個人,就在走廊里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大約九點差一刻,辦公室經理像一陣風似地走了進來,我揪住了他的領子。他就是你們進來的時候我正和他說話的那高個家伙,名字叫萊文——奧斯卡·萊文。”
“辦公室經理,是嗎?”老人說道,吸了一口气。
“是的,長官。他要么裝啞巴要么知道怎么閉上嘴巴,”赫塞接著說,“當然,他已經看過了晨報,對于費爾德的被害感到不安。我看得出來他也不太喜歡我問的問題……我什么也沒有問出來,一件也沒有。他說晚上有事直接回家了……好像費爾德大概四點鐘离開的,再沒有回來……他看了報紙才知道關于謀殺這件事。一上午的時間就這么過去了,等你們來。”
“把萊文給我叫來。”
赫塞回來了,后面跟著瘦瘦的辦公室經理。奧斯卡·萊文外表不太討人喜歡。他長著躲躲閃閃的黑眼睛,异常地瘦。他的鷹鉤鼻子和瘦瘦体態有一种掠奪性。老警官冷冷地打量著他。
“這么說你是辦公室經理,”他說道,“那么,這件事你怎么看,萊文?”
“可怕——真是可怕,”萊文呻吟著說,“我想像不出來怎么發生的,為什么。我的天,昨天下午四點鐘我還和他說話呢!”他看來真地悲傷。
“你和費爾德先生說話的時候他顯得奇怪或者不安嗎?”
“一點也不,先生,”萊文緊張不安地回答,“事實上,他精神特別好,說了個有關巨人的笑話,說他昨晚要去看一場特別好的演出——‘火炮游戲’。我看了報紙才知道他在那里被殺了!”
“噢,他給你講了戲劇的事,是嗎?”老警官問道,“他有沒有偶然說過他和誰一起去?”
“沒有,先生,”萊文挪了挪腳。
“明白了。”奎因停了一下,“萊文,作為經理,你和費爾德的關系比其他任何雇員都親密,你個人對于他知道些什么?”
“什么也不知道,先生,什么也不知道,”萊文急忙說道,“費爾德先生不是一個雇員能親近的人。他偶然說點自己的事情,但總是普通的事情,開開玩笑。對我們這些外人來說他永遠是個体貼、大方的雇主——就這些。”
“他做的到底是什么生意,萊文?你肯定知道些什么。”
“生意?”萊文顯得有些吃惊,“它跟我在法律界遇見的任何行業一樣好。我只替費爾德先生干了兩年左右,但是他有些地位高且很有能力的當事人,警官。我可以給你列張名單……”
“好吧,寄給我,”奎因說道,“這么說他有一個蒸蒸日上、受人尊敬的職業,是嗎?据你所知有沒有私人的來訪者——尤其最近?”
“沒有。除了他的當事人我不記得曾經見過什么人來這里。當然,他也許和他們中的几個人有社交往來。噢,對了!他的男仆有時候來這里——高個、結實的家伙,名字叫邁克爾斯。”
“邁克爾斯?我得記住這個名字,”老警官若有所思地說道。他抬起頭看看某文。“好吧,萊文,就到這儿吧。你可以讓員工下班了。你先不要走,我想辛普森的人馬上就到,他肯定會需要你的幫助。”萊文嚴肅地點點頭出去了。
門一關上奎因就站了起來。“費爾德的私人洗手間在什么地方,赫塞?”他問道。赫塞偵探指了指房間里最里面的一個角落。
奎因打開了洗手間,埃勒里緊緊跟在身后。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小型的、在牆的一角隔出來的立方形空間,里面有洗臉池、一個藥箱和一個小農櫥。奎因先查看了藥箱,里面有一瓶碘酊,一瓶過氧化物,一管剃須膏,還有其他剃須用具。“沒什么東西,”埃勒里說道,“衣櫥呢?”老人好奇地拉開衣櫥的門。那里面挂了一套上街穿的衣服,半打領帶和一項淺頂軟呢帽。老警官把這頂帽子拿到了辦公室查看。他把帽子遞給埃勒里,埃勒里馬上厭惡地把帽子挂回衣櫥的帽釘上。
“那些該死的帽子!”老警官發火了。有人敲門,赫塞領進一位溫和的年輕人。
“奎因警官嗎?”新來的人彬彬有禮地問道。
“是的,”老警官急躁地回答,“如果你是記者,你可以寫警方將在二十四小時之內抓住殺害蒙特·費爾德的凶手。目前我只能告訴你這么多。”
年輕人笑了笑。“抱歉,警官,可我不是記者。我叫阿瑟·斯托埃特斯,地方檢察官辛普森辦公室新雇的人。今天早上才跟我聯系上,我正忙著別的事——所以來遲了。費爾德這件事,太糟了,對嗎?”他咧嘴笑笑,把大衣和帽子扔到椅子上。
“這只是一种觀點,”奎因咕噥道,“他确實惹了一大堆的麻煩。辛普森有什么指示?”
“我對費爾德的職業還不太熟悉,這很自然,我只是臨時代替蒂姆·克洛宁,他今天早上被別的事情纏住了。我先開始干,等蒂姆騰出手,他大概下午能來。克洛宁,你知道,是几年前調查費爾德的那個人。他很渴望處理這些檔案。”
“确實如此。根据辛普森介紹的克洛宁的情況——如果這些記錄和檔案有什么問題,克洛宁一定能把它找出來——赫塞,把斯托埃特斯先生帶到外面去,把他介紹給萊文——他是辦公室經理,斯托埃特斯。盯著他——他像只狡猾的狐狸。斯托埃特斯——你在這些記錄中,不是找合法的生意和當事人,而是找內部不正當的地方……回頭見。”
斯托埃特斯沖著奎因歡快地笑笑,然后跟著赫塞出去了。埃勒里和他的父親面對著面。
“你手里拿著什么?”他父親嚴厲地問道。
“一本‘筆跡告訴你什么’的書,從書架上拿的,”埃勒里懶懶地答道,“怎么了?”
“我們來考慮考慮,埃勒里,”老警官慢慢地說道,“筆跡這東西靠不住。”他絕望地搖搖頭站起來,“來吧,儿子——這里沒有什么可指責的。”
他們走進主辦公室。這個辦公室里現在除了赫塞、萊文和斯托埃特斯外已沒有別人。奎因向赫塞偵探示意了一下。“回家吧,赫塞,”他和藹地說,“不能讓你得上流行性感冒。”赫塞咧嘴笑笑沖出門去。
几分鐘后奎因警官坐在了他位于中心大街的個人辦公室里。埃勒里把它叫做“星級房間”,小、舒适、像家一樣。埃勒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開始精讀那本他從費爾德的辦公室和公寓偷來的關于筆跡的書。老警官摁了下門鈴,托馬斯·維利穩健的身軀在門口出現了。
“早,托馬斯,”奎因說道,“你從布朗·布魯斯商店給我找到什么值得注意的東西沒有?”
“我不知道有多引人注目,警官,”維利冷靜地說,坐在靠牆一排的一張直背椅上,“但我認為听起來很可靠。你昨晚告訴我去查查費爾德的帽子。我桌子上有一項跟他那頂完全一樣的帽子,想看嗎?”
“別說傻話,托馬斯,”奎因說道,“快去拿!”維利走了,又很快抱著一個帽盒回來了。他撕掉包裝,露出了一頂出眾的大禮帽,它的質量那么好,以至于奎因眨眨眼睛。他好奇地拿起這頂帽子,里面標著尺寸:二又八分之五。
“我跟布朗店的店員、老計時員談了。他伺候費爾德多年了,”維利繼續說道,“似乎費爾德的每件衣服都是在那儿買的——很長時間了。恰巧他就喜歡一個店員。這個老貪婪鬼自然地知道了不少費爾德的愛好和買了什么東西。
“他說,一般說來,費爾德對衣服很挑剔。他的衣服總是在布朗店的專門裁縫部訂做。他喜歡花里胡哨的衣服和式樣。近來又喜歡上了內衣和領帶……”
“他對帽子的興趣呢?”埃勒里插嘴道,眼睛沒离開他正看的書。
“我正要說帽子,先生,”維利接著說道,“這個店伙計特別注重帽子的買賣。舉個例子:當我問他大禮帽的時候,他說:‘費爾德先生几乎對帽子著迷。為什么,過去的六個月里他買了不下三頂帽子!’我緊跟著問,當然——讓他查查售貨記錄。确實如此,去年半年里費爾德買了三頂禮帽!”
埃勒里和他父親發現他們正互相瞪著對方,正要問同樣的問題。
“三頂——”老警官說道。
“那么……這可不是正常情況吧?”埃勒里慢慢地問道,伸手去拿夾鼻眼鏡。
“其他兩頂帽子到底在哪里?”奎因用疑惑不解的口气接著問道。
埃勒里一語不發。
奎因不耐煩地轉向維利:“你還發現什么了,托馬斯?”
“除了這一點,沒什么有价值的,”維利答道,“說到衣服,那個費爾德完全到了發狂的地步,以至于去年他買了十五套衣服,不下一打的帽子,包括大禮帽!”
“帽子,帽子,帽子!”老警官呻吟道,“這家伙一定是個瘋子。听著——你是否發現費爾德在布朗店曾經買過手杖?”
維利臉上划過惊恐的表情。“怎么了——警官,”他懊悔地說,“我看我忽略了這件事。我甚至都沒想過要問,你昨晚上沒告訴我——”
“我們當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的,”奎因咆哮道,“給我打電話叫那個店伙計,托馬斯。”
維利拿起桌上的一部電話,過了會儿把電話遞給他的上司。“我是奎因警官,”老人很快地說道,“我了解到你服侍蒙特·費爾德許多年了……那么,我想查一個小細節。費爾德從你們那里買過手杖一類的嗎?……什么?噢,明白了……是的。還有件事。他對他衣服的制作有沒有特殊的要求——多加口袋,或者這類東西?……你認為沒有。好吧……什么?噢,懂了。非常感謝。”
他挂上話筒轉過身。“我們不幸失去的朋友,”他厭惡地說道,“看來對于手杖极其厭惡,正如他對帽子非常喜歡一樣。這個店伙計說他試過許多次想讓費爾德對手杖感興趣,費爾德每次都拒絕買。他說他不喜歡手杖。店伙計證實了他的特別。口袋的印像——沒有。這樣一來我們又陷入了死胡同。”
“恰恰相反,”埃勒里冷冷地說,“不是那种情況,這就完全證明了昨晚上凶手拿去的惟一一件證物是帽子。在我看來事情簡單了。”
“我一定具有白痴的智力,”他父親咕噥道,“我一點也不明白。”
“隨便說一句,警官,”維利插了一句,愁眉苦臉地,“杰米報告了費爾德的瓶子上的指紋。有几個,但是沒有問題,他說,指紋都是費爾德的。杰米從停尸房印了個指紋,當然是為了核對。”
“那么,”老警官說,“也許瓶子与犯罪毫無關系。無論如何我們得等普魯提對瓶子里面東西的化驗報告。”
“還有一件事,警官,”維利又說道,“那些垃圾——戲院里掃出來的垃圾——你讓潘澤今天早上給你送來,几分鐘前送到了。想看看嗎?”
“當然,托馬斯,”奎因說道,“你出去的時候給我把你昨晚上列的沒有票根的人名單拿來。座位號加到每個名字上了吧?”
維利點點頭出去了。當警官拎著一個笨重的包和一份打印的名單回來時,奎因正愁眉不展地看著他儿子的頭頂。他們把包里面的東西小心地攤到桌子上。收集來的東西多半是皺皺巴巴的,几張紙片,主要是糖果盒上撕下來的;許多票報——福林特和他的搜查人員沒有發現的票根;兩只不同花樣的女人手套;一個棕色小扣子,可能是一件男人大衣上掉下來的;一只自來水筆筆帽;一條女人的手帕和其他一些在戲院丟掉或扔掉的東西。
“看起來這里面沒有什么東西,”老警官評論道,“至少我們下面可以核對票根了。”
維利把丟掉的票根堆成一小堆然后開始給奎因讀他們的號碼和字母,奎因對著維利給他拿來的名單核對。票根不太多,核對工作一會儿就干完了。
“就這些嗎,托馬斯?”老警官抬頭問道。
“就那些,頭儿。”
“根据這張名單大約還有五十個人沒有查清楚——福林特在哪里?”
“他在樓里的什么地方,警官。”
奎因拿起電話,快速下令。福林特几乎馬上出現了。
“你昨晚發現了什么?”奎因突然問道。
“警官,”福林特局促不安地答道,”我們几乎把那個地方干洗了一遍。我們找到了不少東西,但是大多數都是節目單之類的東西,那些東西我們留給清洁女工了,她們和我們一起干活。但我們确實撿了一大堆票根,尤其在過道里。”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捆橡皮筋扎得整整齊齊的門票。維利接過來繼續著念號碼和字母的程序。他讀完的時候奎因把那張打印的名單拍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沒什么收獲?”埃勒里低聲說道,從書上抬起頭。
“見鬼!沒有票根的每一個人都查過了!”老警官咆哮道,“沒有漏下一張票根、一個人名……我能做的一件事。”
他在票根堆里翻尋著,對照著名單,最后他找到了屬于弗朗西斯·伊維斯一波普的票根。他從口袋里摸出他星期一晚上收集的四張票根,然后把售票員的票根与費爾德座位的票根仔細檢查。撕的邊對不上。
“我們感到安慰的是,”老警官接著說,把五張票根塞進背心口袋里,“還沒有找到費爾德座位左右和前后六張票的一點蹤跡!”
“我認為你找不到,”埃勒里說道。他把書放下,帶著少有的嚴肅看著他父親。“你就沒有停下來考慮考慮,爸爸。我們知道費爾德昨晚為什么去戲院嗎?”
奎因皺著眉頭。“那個特殊的問題當然也始終困扰著我。据羅素夫人和邁克爾斯講,費爾德不喜歡看戲——”
“你永遠無法預料一個男人會做出什么樣古怪的行為,”埃勒里果斷地說,“許多事情會使一個不愛上劇院的男人突然決定喜歡上那种娛樂活動。事實是——他去了戲院。但我想知道的是他為什么去。”
老人沉重地搖搖頭。“是生意上的約會?記得羅素夫人說的話——費爾德答應十點鐘回去。”
“我贊同生意上的約會這個主意,”埃勒里稱贊道,“但是想想有多少种可能性——羅素夫人也許在說謊,費爾德沒有說那种話,或者即使他說了,他并沒有打算十點鐘跟她約會。”
“我完全承認,埃勒里,”老警官說道,“無論是什么可能性,他昨晚去羅馬戲院不是去看戲,他去那里眼睛睜得大大的——做生意。”
“我個人認為這個看法是正确的,”埃勒里微笑著答道,“但是在判斷可能性的時候細心總不會錯。如果他是去做生意,去見某個人,那個人是凶手嗎?”
“你問的問題太多了,埃勒里,”老警官說,“托馬斯,讓我們來看看包里的其他東西。”
維利小心翼翼地把雜七雜八的東西一件件遞給老警官。手套、自來水筆帽、紐扣和手帕,奎因很快地檢查一下就扔到一邊。除了小包裝糖紙片和皺巴巴的節目單,好像沒有其他東西了。突然,在他檢查當中,他開心地喊道:“看看我找到了什么,小子們!”
三個人傾斜身子越過他的肩膀看去。奎因手中拿著一張節目單,皺折被整平了。節目單顯然是曾被人揉過扔掉了。在里面一頁上,在一篇有關男性服裝的普通文章的邊上,有几個不同的符號,有的組成字母,有的組成數字,還有一些組成神秘的圖案,好像一個人在無所事事的時刻信手涂鴉。
“警官,看起來你似乎找到了費爾德自己的節目單!”福林特高興地喊道。
“是的,先生,肯定是,”奎因嚴厲地說道,“福林特,檢查一下我們昨晚在死者衣服里找到的單据,給我拿一封有他的簽名的信。”福林特匆匆出去了。
埃勒里正在專心致志地研究那些潦草模糊的筆跡。在紙的最上面的空欄處顯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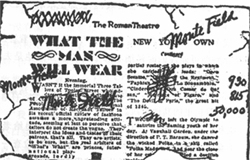
福林特拿著一封信回來了。老警官對比了簽名——顯然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
“我們讓杰米在實驗室驗證一下,”老人咕噥道,“但是這個非常可靠,是費爾德的節目單,這點毫無疑問……你怎么看,托馬斯?”
維利咬著牙說:“我不知道別的數字指的什么,但是那個‘50,000’的意思肯定是指美元,局長。”
“這個老家伙一定是在估算他的銀行存款,”奎因說道,“他很喜歡看他自己的名字,是吧?”
“這對于費爾德不太公平,”埃勒里抗議道,“一個人坐著無所事事的時候,等待什么事情發生——就像他在戲院里等著演出開始的時候——他最自然的行動是在手頭的東西上涂寫他名字的開頭字母或他的名字。在戲院里最靠近手邊的物体就是節目單——書寫自己的名字在心理學上是個基本原則,所以也許費爾德并不像這張報紙上所表明的那么自高自大。”
“這點并不重要,”老警官說道,皺著眉頭研究著那些潦草的筆跡。
“也許吧,”埃勒里答道,“但是回過頭看看一件更為迫切的東西——我不同意你所說的‘50,000’可能是指費爾德的銀行存款。當一個人匆匆寫下他銀行結余時,他不會用整十整十的數字表示。”
“我們很容易就能證明或者推翻這個結論,”老警官反擊道,抓起了電話。他讓警方接線員給他接費爾德辦公室的電話。他和奧斯卡·萊文談了一會儿之后,帶著垂頭喪气的神色轉身看著埃勒里。
“你是對的,埃勒里,”他說道,“費爾德有一筆非常小的個人存款,他所有的存款結余不到六千美元,盡管他經常存上個一万、一万五千美元。萊文自己也很吃惊。他不知道,他說直到我要他查查這件事,他不知道費爾德的個人財政情況……我打賭費爾德的錢都拿去炒股票或者賭賽馬了!”
“這消息我不是非常吃惊,”埃勒里說道,“這就解釋了節目單上‘50,000’的可能原因。那個數字不僅僅表示美元,但更多的是——他表示一种生意買賣,賭注是五万!應該是筆不錯的買賣,如果費爾德能活著做完這筆買賣。”
“其他兩個數字呢?”奎因問道。
“我要仔細考慮一下它們,”埃勒里答道,慢吞吞地坐回到椅子上。“我很想知道什么生意買賣牽扯到這么大的財政問題,”他又說道,心不在焉地擦著他的夾鼻眼鏡。
“不管是什么生意買賣,”老警官故作庄重地說道,“你該肯定,我的儿子,它都是邪惡的。”
“邪惡的生意?”埃勒里用嚴肅的口吻問道。
“金錢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老警官笑著反駁道。
埃勒里的語气沒有改變:“不僅是根源,爸爸,還是果實。”
“又是引用誰的話?”老人嘲笑道。
“費爾丁。”埃勒里沉著地說道。
------------------
郁子的偵探小屋出品 郁子掃校
前一頁
回目錄